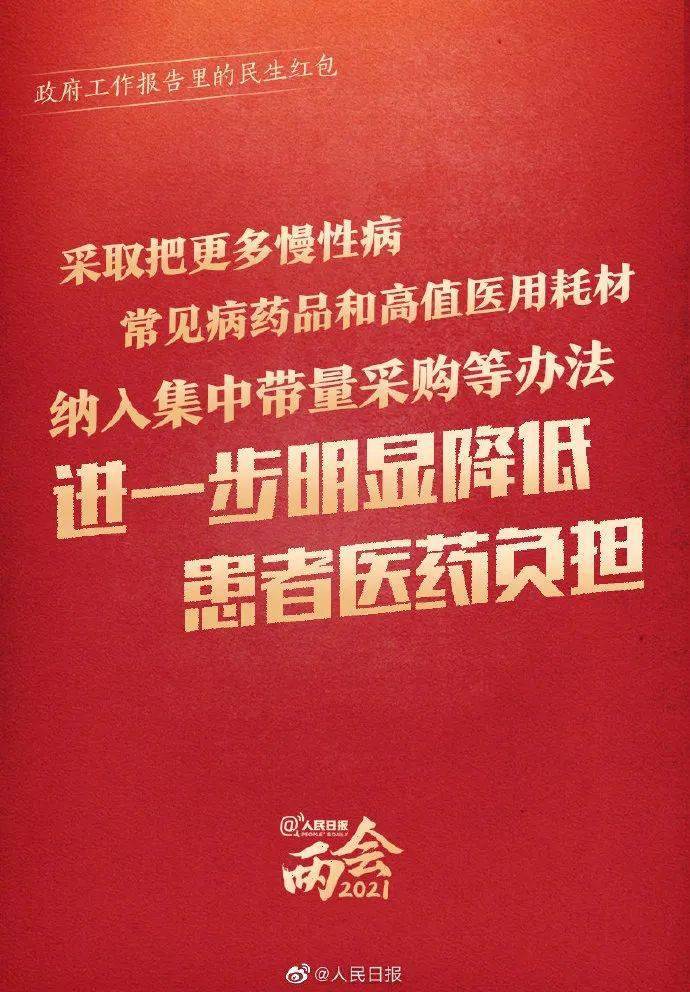
北宋兼职,你了解多少?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宋代,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市民阶层的崛起,“兼职”早已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属概念。无论是为补足俸禄的官员,还是追求经济独立的文人,抑或是手工业者、商贾,都在社会分工的细密网络中寻找着增加收入的途径。然而,与今天灵活多样的兼职形式不同,宋朝的兼职市场既有蓬勃生机,也暗藏着风险——如何找到“安全的选择”,成为当时从业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北宋兼职的兴起,本质上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缩影,而其安全与否,往往取决于渠道的合法性、雇主的信誉度以及社会规范的约束力。
一、北宋兼职:经济活力下的“隐性就业”浪潮
北宋时期,开封府、临安府等百万人口级别的都市崛起,手工业、商业、服务业高度发达,催生了大量非全职岗位。与唐代“重农抑商”的基调不同,宋代统治者鼓励商业发展,“通商惠工”成为国策,这为兼职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等文献记载,汴梁、临安的街巷中,书坊、酒楼、邸店、瓦舍林立,需要大量临时或兼职人员:书坊需文人校勘典籍,酒楼需歌姬乐师助兴,邸店需伙计照料货物,瓦舍需杂技艺人为观众表演。
兼职群体的构成也呈现多元化。官员群体中,低级官员俸禄微薄,如县丞、主簿等职,年薪不足十贯,难以维持体面生活,于是不得不“兼课”(如为私塾授课)、“润笔”(代人撰写碑文、书信)。文人阶层中,未及第的举子常以“抄书”“卖文”为生,欧阳修早年曾“寓僧舍抄书以自给”,便是典型代表。手工业者则多利用农闲时节进入作坊帮工,农民则参与城市运输、建筑等临时工程,形成“离村不离土”的兼职模式。
值得注意的是,宋代兼职的“安全性”首先与职业身份绑定。士、农、工、商的社会等级虽不如唐代森严,但“贱业”仍被主流社会排斥。如《宋刑统》规定,“伎术官”(医官、天文官等)不得兼营他业,而“巫觋、娼优”等职业则被视为“贱业”,从业者即便兼职也难获社会认可。因此,北宋兼职的安全选择,本质上是在“士农工商”框架内寻找符合社会规范的谋生方式。
二、安全选择一:官方与半官方渠道——制度保障下的“铁饭碗”
对北宋从业者而言,最安全的兼职莫过于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提供的岗位,这类岗位有制度背书,薪资稳定,且社会声誉较高。其中,“学官兼职”与“修书兼职”是最典型的两类。
学官兼职主要指地方官学、书院的教职。宋代官学体系发达,从京师国子学到府、州、县学,均需大量“直讲”“教授”辅助教学。这些职位虽多为半职,但由官府任命,薪资由财政拨付,且有“职田”(政府提供的土地补贴)作为补充。例如,庆历四年(1044年)范仲淹推行“庆历兴学”,要求各州县学设置“学职”,允许未任满的官员或致仕官员兼任,既解决了师资短缺问题,又为兼职者提供了稳定收入。王安石变法期间,推行“三舍法”,更是扩大了学官兼职的规模,许多寒门文人通过担任“学录”“学正”等职,实现“以学养家”。
修书兼职则是文化繁荣的直接产物。宋代重视典籍整理,朝廷设“崇文院”“秘书省”等机构,组织文人校勘、刻印书籍。如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等类书的编纂,均招募了大量“兼职”学士参与。这些工作无需全天候在岗,学者可在家中完成校勘,按字数或篇幅领取酬劳。更难得的是,参与修书可接触皇家藏书,对文人提升学术声望大有裨益,堪称“名利双收”的安全兼职。南宋学者叶梦得在《石林燕语》中提到,当时“士大夫之退闲者,多以修书为职,既免远役,复得厚禄”,足见其吸引力。
此外,地方官府的“临时差遣”也属于安全范畴。如修筑河堤、整治道路等工程,官府会招募“夫役”,并按日发放“工食”(粮食与铜钱)。这类工作虽辛苦,但有官府监管,杜绝了雇主克扣薪资的风险,成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重要兼职选择。
三、安全选择二:文化服务与商业辅助——市场规范下的“可持续谋生”
若说官方兼职是“体制内”的安全选项,那么依托市场规则的文化服务与商业辅助,则是“体制外”更普遍的安全兼职。宋代商品经济的成熟,催生了大量服务型岗位,这些岗位虽无官方背书,但通过行业自律和契约约束,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。
文化服务类兼职以“书坊校勘”“私塾塾师”“书画装裱”为代表。宋代印刷业发达,汴梁、临安、建阳(今福建建瓯)成为三大刻书中心,书坊为提升书籍质量,常聘请“校勘先生”对书稿进行校对。如建阳麻沙书坊,便与当地文人签订“校书契约”,约定“错一罚十”,既保证了书籍质量,也保障了校勘师的收入。私塾塾师则是另一重要兼职,富商或官员子弟因家塾教师不足,常邀请落第举子或致仕文人担任“西席”,薪资按学期或学年结算,并有“束脩”(学费)作为额外收入。朱熹未中进士前,曾在福建崇安等地担任私塾塾师,“束脩所入,足以养母”,便是典型例证。
商业辅助类兼职则包括“账房先生”“行老”“铺掌”等。宋代商业分工细化,大型商号需专人负责账目核算,于是“账房”成为热门兼职。这些岗位要求从业者熟悉“四柱结算法”(旧管+新收-开除=实在),且需通过“保人”(担保人)推荐,确保信誉。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汴梁的“金银彩帛铺”常雇佣“老成练达者”为“掌柜”,负责日常运营,薪资为“月钱+分红”,风险极低。“行老”则是行业中介,由各行会推选资深从业者担任,负责协调雇主与雇员的关系,如“雇觅人力”“评定物价”,其兼职收入来自“行佣”(佣金),因有行会监督,鲜有欺诈行为。
值得一提的是,宋代商业契约制度的发展为兼职提供了法律保障。据《宋刑统》规定,雇佣双方需签订“雇契”,明确工作内容、期限、薪资及违约责任。如淳熙年间(1174-1189年),临安一酒坊雇佣“歌姬”一名,契约中写明“月薪三千文,供膳宿,若无故辞退,赔银五两”,这种契约约束虽无现代法律效力,但依赖行会和舆论监督,违约者将面临“行业抵制”,因此雇主与雇员都会自觉遵守,极大提升了兼职的安全性。
四、安全选择三:技艺服务与公益参与——社会网络中的“隐性保障”
除了官方与市场渠道,宋代社会网络和公益组织也为兼职提供了“安全垫”。技艺服务类兼职如“坐堂医”“针灸师”“风水先生”等,依托专业技能和口碑传播,形成了稳定的客户群体。宋代医学发达,官府虽设“太医局”,但民间医疗需求巨大,许多“儒医”(懂医术的文人)在药铺或家中坐诊,通过“脉金”(诊费)和“药费”获得收入。如《夷坚志》记载,汴梁名医张济,“每诊一人,取钱百文,贫者则施药”,其医术精湛,患者络绎不绝,兼职收入远超普通官员。
公益类兼职则更具宋代特色。如“义庄”的管理者、“漏泽园”的守墓人、“粥厂”的帮厨等,这些岗位由地方士绅或官府设立,服务对象为孤寡贫弱,虽薪资微薄,但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。范仲淹在苏州创办“范氏义庄”,规定“义庄管理者由族人推选,负责田租收缴与粮食分发,月给钱三千文”,这种兼职既照顾了族人,又为管理者提供了稳定收入,成为“义利兼顾”的典范。此外,佛教、道教寺院的“知客”“典座”等职位,也属于兼职范畴,寺院提供食宿,并发放“香火钱”,工作内容为接待香客、管理斋堂,工作强度低,安全性高。
五、北宋兼职的“安全法则”:从渠道到契约的自我保护
综合来看,北宋兼职的安全选择并非偶然,而是从业者基于社会规则、市场机制和自身条件作出的理性判断。其“安全法则”可总结为三点:一是“渠道正当”,优先选择官方、行会或信誉良好的雇主,避免参与“走私”“赌博”等非法活动;二是“契约明确”,通过书面或口头契约明确权责,借助保人、行会等第三方监督;三是“身份匹配”,避开“贱业”,选择符合自身社会阶层的兼职,维护声誉与长远发展。
这些法则对现代职场仍有启示意义。在灵活就业成为趋势的今天,北宋兼职的安全机制——制度保障、市场规范、社会网络,恰是当代兼职市场需要借鉴的内核。无论是为书坊校勘的文人,还是为酒楼服务的伙计,他们都在用智慧和规则,为自己编织一张“安全网”,这或许就是千年之前,那个繁华时代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经验。
北宋兼职的故事,不仅是历史的回响,更是对当下“如何安全地谋生”的深刻回答:在充满机遇的市场中,唯有坚守规则、依托信誉、选择正当渠道,才能让兼职真正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阶梯。快行动起来,但请记得,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